
新闻活动

新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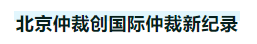
6月12日,2025北京CBD论坛暨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涉外法治发展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杨公布一组数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以101天平均结案周期打破国际仲裁效率纪录,裁决国内执行率接近100%,在最新国际仲裁报告中,北京首次跻身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四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涉外法治更是对外开放的“稳定器”。近年来,北京司法行政系统创新构建“1+N”商事争议解决服务体系,推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解纷机制深度融合,打造“一站式”涉外法律服务高地。目前,北京41家律所已在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361个境外办公机构,服务网络覆盖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法治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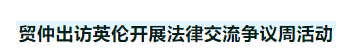
6月1日-3日,在2025伦敦国际争议周(LIDW 25)期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率代表团在伦敦积极展开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法律交流活动,以增进业界了解、深化专业合作。
贸仲代表团围绕争议解决主题,精心策划并举办了在英中资企业座谈会、贸仲在英仲裁员圆桌座谈会及“一带一路”争议解决国际仲裁研讨会系列活动,邀请中英法律界专业人士共探仲裁实务与跨境争议解决前沿议题。交流中,各方围绕国际仲裁实践的最新趋势、跨境争议解决中的难点与热点、“一带一路”沿线争议解决机制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国际仲裁领域开展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为促进中英法律界互信与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贸仲代表团赴英交流,以增进了解、深化合作为目标,通过多场专业活动与广泛走访,与英国法律界达成加强争议解决合作的共识。代表团行程紧凑高效,既展现了中国国际仲裁的专业形象,也为中英法律界搭建了长效沟通桥梁,标志着双方在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交流迈向新台阶,英伦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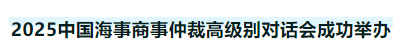
6月6日,2025中国海事商事仲裁高级别对话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对话会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海仲”)主办,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香港航商总会等5家机构协同合作,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伦敦国际仲裁院、俄罗斯工商会海事仲裁委员会、新加坡海事仲裁院、韩国仲裁人协会、开罗区域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等15家国内外机构支持参与。
本次对话会以“推进海事仲裁制度创新、打造世界一流仲裁机构”为主题,邀请近30位境内外知名业内专家展开对话和研讨,深化国际仲裁交流合作,共谋国际仲裁发展大计。来自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全国贸促系统及境内外法律界、企业界、学术界等方面的代表现场参会。
成果发布环节,中国海仲发布了《自贸区企业海事海商典型案例集》,汇编了中国海仲具有代表性的10个典型案例,及时总结自贸区企业海事海商争议解决的独特实践经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导作用,稳定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引导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为我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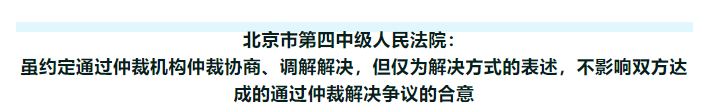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案情简介:
2014年5月14日,甲方某照某公司与乙方某机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为:“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时双方同意选择下列第1)种方式予以解决:1)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通过协商、调解解决。2)对于本合同在执行中发生的争议,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申请人(原告)某机某公司主张该条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仲裁协议必须包含“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的规定,请求法院认定为无效。被申请人(被告)某照某公司未应诉答辩,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法院观点:
法院认为,案涉条款存在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施工合同》第十三条中第1)种方式约定的内容“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其中明确包含了“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的表述。虽然其后约定“通过协商、调解解决”,但这仅是对仲裁过程中可能采用的解决方式(如仲裁调解)的描述或建议,并不否定或替代双方达成的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核心合意。该条款解决的是“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时”的争议,指向因《施工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仲裁事项明确。“北京仲裁委员会”的名称表述清晰、具体,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明确无误。
案涉仲裁条款不存在《仲裁法》第十七条(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或第十八条(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未能达成补充协议)规定的无效情形。
案涉《施工合同》第十三条争议解决条款(第1)项)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的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形式要件。“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表述,仅涉及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中可采用的内部解决纠纷方式(由仲裁机构根据仲裁规则确定),不影响双方达成仲裁合意的有效性。
因此,法院认定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裁定驳回某机某公司的申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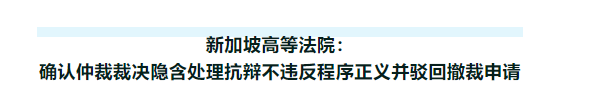
案情简介:
2014年10月10日,公司、两位发起人(本案第一、第二原告,亦为仲裁被申请人)与投资者(本案被告、仲裁申请人)及另外两方当事人,联手签署了《股份收购与股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第19条约定:若公司未能在2016年3月31日前完成合格首次公开募股(Qualified IPO),投资者可先行发出“二级出售启动通知”要求以不低于“退出价格”出售其持股;若二级出售无法落实,公司及发起人则须回购该等股份;若回购亦失败,双方应启动IPO;若公司存在重大违约(包括拒绝提供退出机会),投资者可直接将公司全部股权出售予第三方,称为“战略出售”。第24条进一步明确了违约责任,其中第24.4(c)款将未依第19条提供退出属于重大违约,第24.6(b)款则赋予投资者回购权。
2016年4月—26日,第四、第二、第三位投资者相继依据第19.1条发出二级出售启动通知,但由于未寻得合适买家,二级出售迟迟未能完成。2020年9月18日,第二、三位投资者再次致函公司,要求任命银行家推动交易;2021年1月5日,第一位投资者亦正式敦促完成二级出售或启动IPO;2022年4月11日,投资者基于重大违约再度发函,4月14日与21日启动仲裁,并于4月30日合并审理。仲裁庭于2024年7月5日认定:第19.1条确立了公司与发起人“不折不扣”寻找二级市场买家的绝对义务;投资者的多次启动通知有效;公司与发起人已严重违约,应按照2020年9月18日标准的“退出价格”赔偿投资者损失,赔偿额可抵扣其通过战略出售所得收益,投资者在获赔后将股份返还公司。
法院观点:
法新加坡高级法院在审理发起人OA 1033号撤裁申请时,对仲裁庭是否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和是否超越酌情裁量范围进行了深入评析。法官的核心观点可归纳如下:
1. 司法审查的法定框架
根据《国际仲裁法》(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第24条,新加坡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仅限程序公正(natural justice)瑕疵或裁决超越仲裁协议或仲裁庭权限的情形,而不涉对裁决实质内容的再评审。只有当仲裁程序确实剥夺当事人陈述抗辩的实质机会,或仲裁庭认定的事实与其程序记录严重不符时,法院才会介入。
2.“隐含驳回”原则的适用
法官援引ASG v ASH [2016] 5 SLR 54、TMM Division Maritima SA de CV v Pacific Richfield Marine Pte Ltd [2013] 4 SLR 972等判例,确认仲裁庭可通过其“裁决逻辑”与“事实认定”隐含地处理当事人的抗辩,无须在裁决文书中对每一项辩点作出逐条回应。只要裁决中体现了对此抗辩事项的考虑和否定,即视为合规。
3. 对“弃权抗辩”(Waiver Defence)的分析
事实认定:仲裁庭详细记录了投资者多次以书面及会议形式明确援引协议第19.1条,要求启动二级出售程序,并批准了瑞士信贷作为交易顾问。依据协议第29.5条,任何放弃权利须“书面形式”明确,否则无效。发起人无法提供任何书面弃权文件。因此仲裁庭对投资者主张权利的持续性与对放弃要求书面形式的法律考量,构成对弃权抗辩的实质性审查与否定,不存在程序性遗漏或偏见。
4. 对“回购抗辩”(Buy-back Defence)的细化
解释层面:发起人认为,第19.1条损害赔偿等同于“隐性回购”,应按印度公司法回购限制审查。法院指出,仲裁庭在裁决段落(特别是[332]、[370]、[372]、[381])已明示:赔偿义务为普通法下的金钱救济,与协议第24.6(b)条规定的正式回购机制截然不同。
可执行性层面:即便损害赔偿被视为回购后果,发起人并未在仲裁或诉讼中举证证明此种补救违反印度公司法禁止性条款;更何况,解释层面抗辩已遭否决,其“不可执行性”抗辩自失前提。
程序正义:发起人主张仲裁庭未对回购抗辩“逐点回应”,但法院重申,隐含驳回同样有效,且仲裁庭口头听证及裁决文本已表明对该抗辩的理据判断,发起人未能证明因此遭受实体权利损害。
5. 对《纽约公约》公共政策考量的确认
法院进一步强调,出于对新加坡作为国际仲裁中心地位的维护及对跨国商业仲裁的尊重,只有在严重违背公共政策或实质否认程序公正时,才会否定或撤销外国仲裁裁决。本案中,仲裁庭的程序和实体处理均符合法律和协议约定,不触及公共政策的底线。
综上,新加坡高级法院认为仲裁庭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保障方面均无不当,发起人的两项撤裁理由均无立足之地,裁定驳回发起人的撤裁申请,维持仲裁裁决的效力。
